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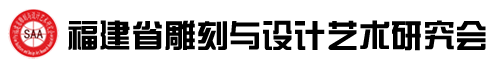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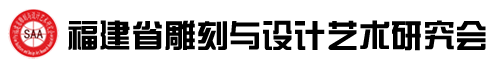

王长坤雕刻的古兽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引人的眼球,仿佛穿越到上古时期,神魔世界。
形态各异,从未见过的远古神兽在王长坤的想象世界中逐渐成型,而后在他的笔和刀下具像化。它们有的庄严肃穆,有的威武雄壮,有的又憨态可掬,情致可爱。这种拟人化的创作手法,既充满神话色彩,又倾注人间温暖,创作者似乎把自己的精神与生命力注入到这古兽当中,带人一起徜徉一个遥远而又不可思议的世界。

左起:王长坤正在雕刻;王长坤作品《九狮戏球》
“我并不是一毕业就去做寿山石雕,进入这个圈子完全是因为一种兴趣爱好,因为对美的事物有向往和追求。”王长坤是美术专业出身,最早是对古玩有一定的兴趣和了解,后来在朋友的带领下了解到寿山石雕,慢慢地也就对寿山石产生了兴趣。他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专门做雕刻,只是收藏,买了一些原石,有时候也会请雕工或者大师帮忙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出于精益求精的需求,后来他就开始对工具进行一些改进,慢慢地就有动手的欲望。1994年他踏入了玉石雕刻领域后,向寿山石雕刻大师学习,并将中西艺术进行融合,自成一派。

王长坤作品《中华龙脉》
雕刻这个板块一般分为人物、山水这几类,但是这几类都不适合过度的艺术的夸张。雕刻的基础都是写实,而人物必须要写实。古兽既可以写实,又可以进行一定的艺术处理。“我觉得古兽更生动,创作时不拘一格,从创作层面来深入,则包含了更多的中国传统人文元素,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来进行艺术处理和加工,以更多的写意为主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《山海经》的故事,我通过古兽这种载体把它展现出来。”写实的作品因为有参照物,所以相比写意来说更容易创作。“比如说我要雕刻人物,可以让人物坐或者站在那里摆个动作,然后照着刻就行。只要你在院校里呆上五年十年,基本上都能达到一定水平。我当时选择做古兽,也是因为我认为还有更大的艺术语言在这里面。我个人喜欢这样有更多创作空间和想象空间的东西,你没有参照物,又要符合这个力学、空间感、体积感,美感,同时还要有合理的结构和布局,这有很大的挑战性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,有意思的。”说到雕刻题材的选择问题上,王长坤侃侃而谈。

上图:王长坤作品《谛听》《蚣蝮》
王长坤的创作选材广泛,寿山石、象牙、琥珀、木雕等,猛犸、和田玉、翡翠、鹿角包括木头都有涉及。“应该说我不是专注于玉石雕刻这一块,其他的手工艺也很多,但只要跟雕刻相关的我都有涉及。”他的作品包罗万象,海纳百川。古兽神形兼备,具有独创性的结构和综合立体感,突出古兽的气势与神韵。在某个阶段,王长坤很喜欢早期商秦风格,“因为有功绩,有庙堂之气,象征着贵气,而且很端庄、很稳重。”那个时候作品都会往这个风格靠近。但如果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创作的话,也会觉得无趣。而在另一个阶段,他又喜欢上欧美的东西,“结构更强烈,体会更明显,甚至创作的时候,会用欧美文化元素来做启发,这样子做了一段时间,又觉得无趣,又回到我们中国的传统这里来。”王长坤对艺术家在创作上的“喜新厌旧”毫不避讳:“其实人就是这样的,在创作过程中,进进出出,不断寻找,有时候我们会利用业余时间去寻找一些偶然,与人交往、聊天、沟通,或者说去哪里逛逛,偶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灵感。有了灵感的时候,我们就按这个定位去思考、去创作,这样总是会有新的想法出现。有的时候眼前突然闪现的一个场景,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,甚至一首歌,一段音乐,它都有可能的。”

王长坤正在雕刻
“艺术风格的变化有时候真的是突发性的,他可能一直走某个风格,某天就突然转变过来,因为当灵感涌现的时候是无法阻挡那种冲动和欲望的。”王长坤就是这样不断地追寻自己喜欢的东西。“每一个阶段的喜好都是在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种需求,如果说没有变化,就相当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局限了。人要有这种所谓的少年张狂的心态,不断改变,大胆创新。”艺术界是最讲究创新的领域。在王长坤看来,真正的创新是一种自内而外的状态,是自我最好的迸发,是内心深处的呐喊。创新应该是源自思想上,而不是为了迎合市场,刻意去创新,为创新而创新,真正的创新是一种艺术上的方法。有句话说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,说得就是这种艺术手法。北宋徽宗朝廷“以踏花归去马蹄香”为主题来挑选画师,有的人着重“花”这个字,画了许多花瓣;有的人煞费苦心在“马”字上下功夫,主体突出马的奔腾飞跃;有的人不拘一格,画了一只大大的马蹄子。而有个人独辟蹊径,画了一个马踏蝶舞的情景,那说明他骑着马踏过花丛并且沾染上花的香味,蝴蝶闻到花香跟随过来。这就是很有技巧的一种表现,不是那种很平铺直叙、浅显直白的创作手法。“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突破,一种非常规的创新。创新就是碰撞出思想上的火花,让我重新感受到创作的活力。”王长坤如是说。

上图:《 腋下之目》《唐狮》
“我有一个习惯,我不愿意去做重复性很高的事情,这样会失去乐趣。我不断去寻找一些能够让我有感觉的想法去创作。“王长坤的艺术之路不愿创重复之作,既为致敬传统,又为立足新时代进行创新。《腋下之目》这件作品便是如此,饕餮骨骼线条突出,肌理结构接近亚光,皮肤纹理略带粗糙,扭身的动作展现了动态,整个作品充满了真实感和原始感。西方的写实主义和东方文化的“包容性”均有所体现。“古兽应该是有皮、有肉、有骨骼的,印纽不一定要摸起来圆润才是好,在创作中保留古兽的骨血,也是我对美的一种理解和表达。饕餮的吃,就是一种包容,不管你是东方、西方,我都可以消化、吸收。”从业25年来,王长坤以古兽为题材,在中国历代的印纽雕刻历史长河中追本溯源,源源不断汲取现代雕塑创作的养分,重构传统寿山印纽技艺与现代雕塑语言,探索思想、文化、艺术的融合。其将古兽拟人化的创作手法,打破了传统造型与时代感之间难以融合的壁垒。正所谓“用心精至自无疑,千万人中似汝稀。”